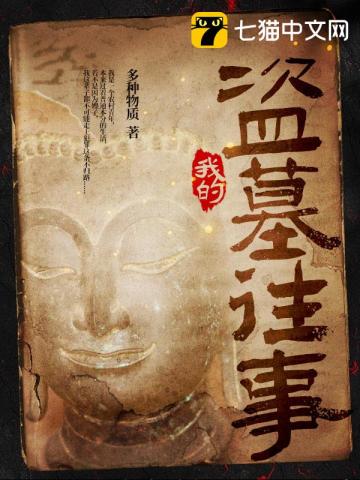泥巴文学 > 《孤岛余生》作者 :陈之遥 > 第101章(第2页)
第101章(第2页)
她彼时的目光一直留在他脑海中,那种看陌生人的目光,仿佛八年的离别没能分开他们,生活在一起的几个月却把这八年轻易地抹去了。
这是最叫他耿耿于怀的细节,他们之间竟然连一次像样的告别都没有。
这遗憾,唯有在短暂梦里才会短暂地忘却。
那两夜,他不出意外地失眠。凌晨入梦,总是回到他们在香港的时候,还有后来一直通信的三年。其实,那才是他们之间最好的时光,虽然稍纵即逝,虽然远隔重洋。但在那个岛上,在那些信里,她是真正的她,他也可以只做他自己。
某一秒的梦中,他又回到浅水湾,在月色下对她道:“你已经变得更好,我却没有,甚至比从前还要坏。”
“我哪里变了?”她走过来,离他很近很近。
“是个大人了。”他看着她,伸手拨开她的额发,仿佛忽然洞悉未来,只想告诉她走吧,不要再回来,你已经不需要我了。
“大人?”她却浑然不觉这是一场告别,踮脚上来在他耳畔道,“我怎么记得,老早就跟你做过许多大人才能做的事情?”
梦醒,便再无遗憾。一切都是命定的,他舍不得早一点放弃她,在一起的每一秒都过得万分值得。走到今日,也只需做完眼前这件事就可以了。
第三天,该来的终于来了。
那时已是深夜,宵禁就要开始,街上不见行人,远处有骑警经过,只听见马蹄踏在铁藜木砖上发出的声音,却又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。原本并不算太宽阔的十字路口显得旷荡一片,有如猎场。
唐竞慢慢踱出哈同大楼,汽车就停街对面。路灯早已经停用,他在月色下走,而后穿过马路,停下来点烟,身后传来微不可闻的脚步声。他没有回头,由着脚步渐近,一管枪口抵在脑后。
“听说唐律师有话要讲?”枪主人开口。
唐竞认得那声音,吐出一口烟,笑道:“得胜,这几年你也是高升了啊。”
“有话就讲,”赵得胜打断他,无意寒暄,“都是老相识,不会叫你走得太难看。”
唐竞却还是抽着烟,缓缓道:“我这话只对张帅一个人说,要不要听,就请他老人家随意吧。”
赵得胜抬手,一记枪托砸下。唐竞倒下去,只觉重击,无有痛感。继而血模糊了视线,他隐约看到另外两张的面孔,认得的,不认得的,随后便没了知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