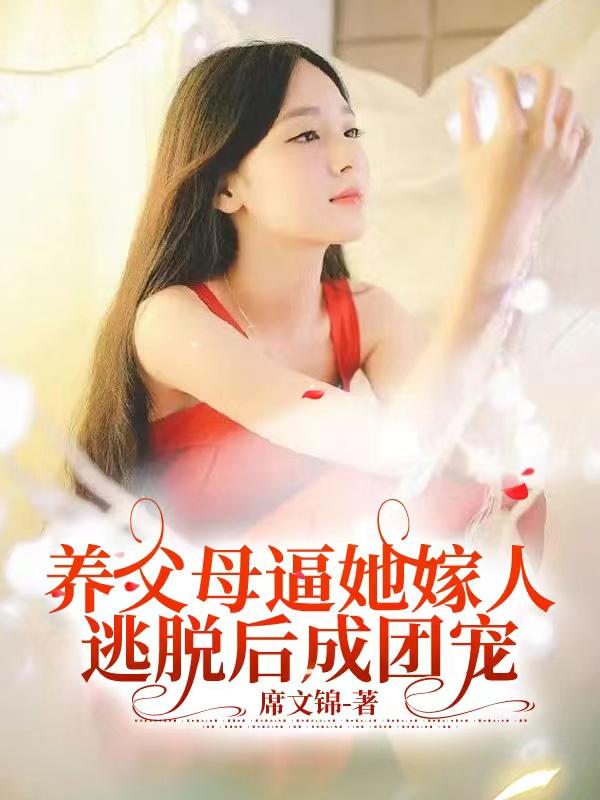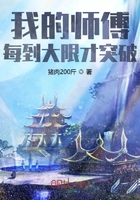泥巴文学 > 岐黄手记 > 第361章 疫情通报·水样便的蔓延(第2页)
第361章 疫情通报·水样便的蔓延(第2页)
诊室里的吊扇慢悠悠转着,吹不散突然凝重的空气。苏怀瑾指尖在桌面上轻轻画着圈,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:“水样便属‘水湿下注’,畏寒是‘寒象’,无感染指征排除‘实邪’,再加上潮湿环境——这很可能是中医说的‘外感湿邪’引发的泄泻。”
她看向镜头,目光扫过参会的西医专家:“能不能麻烦张主任收集一份详细的舌象和脉象记录?比如舌苔颜色、厚薄,脉象是浮是沉、是快是慢——尤其是‘濡缓脉’(按之如裹棉)的出现频率,这对辨证至关重要。”
挂了会议,陆则衍递来一杯刚泡的姜枣茶,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。“濡缓脉?你怀疑是寒湿?”他记得苏怀瑾讲《伤寒论》时提过,“太阴病的脉象多濡缓,主脾虚湿盛。”
“还需要舌象佐证。”苏怀瑾捧着茶杯,掌心的暖意慢慢渗进指尖,“但现在看,环境湿、症状寒、无感染——这更像‘寒湿困脾’,而不是细菌病毒感染。如果舌象是白腻苔,那基本就能定了。”
窗外的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灰布,风卷着远处的雷声滚过来。苏怀瑾望着药圃里被雨水打蔫的薄荷,忽然想起祖父常说的“医贵知时”——老祖宗早就说过“湿盛则濡泻”,遇上连阴雨,脾胃弱的人最易受湿邪侵袭。
她把姜枣茶凑到嘴边,温热的茶汤滑过喉咙时,心里忽然生出个念头: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,或许正是让中医“外感病诊疗”走出诊室,站到公共卫生前线的机会。就像那些被雨水打蔫的薄荷,看似柔弱,却能在需要时散出醒神的气——中医的智慧,或许也能在西医无头绪的时刻,找到破局的方向。
陆则衍的手机响了,是邻市急诊主任打来的,他接起电话,听了两句后突然提高声音:“舌象?好!我们现在就组织老中医去诊室看舌象、摸脉,半小时后给你传汇总!”
挂了电话,他看向苏怀瑾,眼里的焦虑淡了些,多了点期待:“他们说已经找了两位退休老中医去支援,很快就能有舌脉记录——说不定,你真能找到西医没看到的关键。”
苏怀瑾放下茶杯,杯底的枣核沉在杯底,像颗定盘星。她翻开笔记本,在第一页写下:“邻市腹泻疫情——待查:舌象(苔色、厚薄)、脉象(浮沉、缓急)、饮食史(是否生冷)”,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,在阴沉的诊室里格外清晰,像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硬仗,悄悄磨亮了武器。
喜欢岐黄手记请大家收藏:()岐黄手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