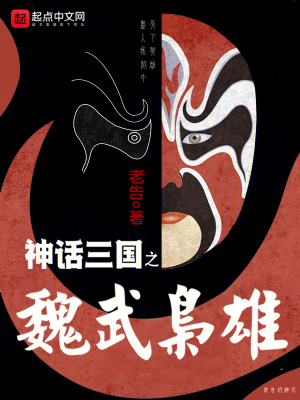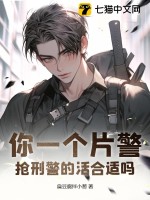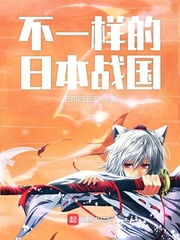泥巴文学 > 岐大夫的悬壶故事 > 第323章 岐仁堂急救:一口阳气系生死(第2页)
第323章 岐仁堂急救:一口阳气系生死(第2页)
他称了一两野山参,又取了四钱白芨,放在研钵里细细研磨。"人参要选野山参,药力足,能大补元气,就像给快熄灭的火堆添上干柴。白芨能止血,还能修补胃黏膜,就像给破了的袋子打上补丁。"
药研成细粉,他又吩咐陈嫂:"去烧点米汤,要稠稠的那种,放温了拿来。"
米汤拿来后,岐大夫把药粉倒进去,调成糊状,搓成樱桃大小的丸子:"这样含在嘴里,慢慢化了咽下去,就不会吐了。"他捏起一颗,轻轻放进吴明初嘴里,"让他含着,别催他。"
陈嫂赶紧上前,用手托着丈夫的头,帮他慢慢吞咽。药丸在嘴里慢慢融化,带着人参的甘苦和米汤的清甜,吴明初的喉咙动了动,竟真的没吐。
"从黄昏到半夜,大概要用到一半。"岐大夫叮嘱,"如果他渴了,就少喂点米汤,千万别喂冷水、凉茶。"他又写下个方子,"这是备用的,等他不吐了,能喝进汤了,就按这个方子抓药。"
陈嫂看着方子上的"人参三钱,附子一钱,干姜一钱,炙甘草一钱",不解地问:"这里面怎么没有止血的药?"
"现在血吐得厉害,是因为气固不住血。"岐大夫解释,"就像袋子破了,装不住东西,光堵窟窿不行,得先把袋子撑起来。人参补气,附子回阳,干姜温胃,甘草调和——这是《伤寒论》里的四逆汤加人参,专门救这种阳气虚脱的。等阳气回来了,血自然就止住了。"
那天晚上,岐仁堂没关门,陈嫂守在丈夫身边,时不时喂一颗药丸。岐大夫就坐在旁边看书,时不时过去看看吴明初的脉搏、呼吸。半夜子时,吴明初忽然哼了一声,嘴唇动了动,陈嫂赶紧喂了点米汤,这次竟咽下去了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"不吐了!真的不吐了!"陈嫂惊喜地叫起来,"他刚才还咽了口米汤!"
岐大夫过去诊脉,脉象虽然还弱,但比之前有力了些,不像刚才那样飘忽了。"好,阳气开始回来了。"他让陈嫂按方子抓药,"现在可以煎药了,小火慢煎,煎出一小碗就行,温着喂他。"
第二天一早,吴明初眼睛能睁开一条缝了,看见陈嫂,虚弱地说:"水。。。。。。"陈嫂赶紧用小勺喂了点药汤,他皱了皱眉,却没吐。
岐大夫来复诊,诊脉后说:"脉像芤脉,又像革脉,还是虚得很,不过总算把阳气拉住了。"他又看了看舌苔,"舌面还是干,说明阴血也伤得厉害,但现在还不能补阴,得先把阳气扶起来。《难经》说阳脱者,见鬼,他昨天是不是说胡话了?"
陈嫂惊讶地说:"是啊!昨天下午他迷迷糊糊地说看见他爹了,要跟他走,吓得我赶紧掐他的人中。"
"那就是阳气快脱了,差点被阴邪拉走。"岐大夫说,"继续用参附汤,人参加到五钱,附子加到二钱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