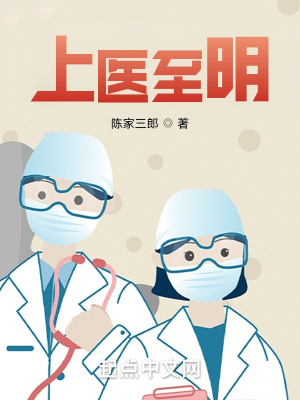泥巴文学 > 岐大夫的悬壶故事 > 第336章 浑身发燥像枯柴,反添柴火春意来(第1页)
第336章 浑身发燥像枯柴,反添柴火春意来(第1页)
六月的日头刚爬到电线杆顶,张翠兰就把刚晒好的被单拽了下来。"这鬼天气,刚晒透就返潮。"她嘟囔着,指尖划过被单时,指腹的裂口又渗出血珠。五年来,她就像块被晒透的老木头,浑身上下找不着一点水润气儿——嗓子眼总像塞着团棉絮,半夜渴醒得咕咚灌半瓢凉水;眼角干得发黏,看会儿手机就模糊成一团;连脚后跟都裂着纵横交错的口子,穿布鞋都硌得慌。
"又拽被单干啥?"丈夫王建国拎着菜篮子进门,塑料袋摩擦的沙沙声在她听来格外刺耳。
"你自己闻闻,一股霉味!"翠兰猛地转身,眼角的皱纹因为干燥更显深刻,"跟你说过多少回,买菜别用塑料袋,不透气!"
王建国把菠菜往案板上一放,蔫黄的菜叶簌簌掉渣:"这不是赶时间嘛。上周李大姐说城里岐仁堂的岐大夫能耐,要不咱明天。。。"
"不去!"翠兰的声音陡然拔高,耳后那股熟悉的燥热又窜了上来,"前儿个喝的那碗滋阴汤,舌头都麻了,照样口干!"她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子猛灌,凉水滑过喉咙时,反倒像浇在烧红的铁板上,泛起一阵灼痛。
后半夜,翠兰又在寅时醒了。窗外的蝉鸣刚起个头,她摸黑摸到尿盆边,这已经是今晚第三次起夜。尿色清得像井水,可喝下去的水怎么也留不住。她对着镜子照,眼窝陷得像两个小坑,舌头伸出来,白腻腻的苔上裂着道深沟,活像久旱的田垄。
"去看看吧,建国在厨房烙了你爱吃的糖饼。"第二天清晨,婆婆把热乎乎的饼子往她手里塞,"昨儿个我去公园遛弯,见着三楼的赵婶,她说她闺女前几年也这样,就是岐大夫看好的。"
岐仁堂藏在老城区的巷子里,朱漆门楣上的"岐仁堂"三个字被雨水洗得发亮。药柜前的岐大夫正低头称药,戥子上的当归片薄如蝉翼。听见动静,他抬起头,目光落在翠兰脸上时顿了顿——两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,可手背却青白色,像泡在井水里的萝卜。
"坐。"岐大夫指了指竹椅,"伸舌头我瞧瞧。"
翠兰刚把舌头伸出来,就听见岐大夫"嗯"了一声:"苔白腻,中根有裂,这是水湿困住了阳气啊。"他指尖搭在她腕脉上,三指轻轻一按,眉头便皱了起来,"脉沉细,阳气虚得厉害。"
"大夫,我这是咋了?"翠兰的声音带着沙哑,"喝了多少梨水、银耳汤都没用,反而越喝越渴,手脚还冰凉。"
岐大夫往紫砂壶里添了把龙井,沸水冲下去时,茶叶在水里打了个转儿又沉底:"你这不是缺水,是灶膛里没火了。"他指着药柜上的《黄帝内经》,"书里说阳气者,若天与日,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。你这身子就像口井,井底下的泉眼堵了,光往井里倒水有啥用?得把泉眼通开。"
王建国在旁边插了句:"前几个大夫都说她是上火,让多吃凉的。"
"错喽。"岐大夫把茶杯推给翠兰,"你摸摸这杯子,外面烫,里面才能泡出茶味。人也一样,阳气就是那灶火,火不旺,水怎么能变成蒸汽润到全身?《伤寒论》里说自利不渴者,属太阴,以其脏有寒故也,当温之,宜服四逆辈,你这情况,就得用些热药把阳气扶起来。"
翠兰捧着温热的茶杯,掌心终于有了点暖意:"可我总上火啊,耳后动不动就烧得慌。"
"那是虚火。"岐大夫拿起戥子称附子,乌黑的药块在铜盘里发出轻响,"就像烧乏了的煤球,表面看着红,底下早凉透了。这种火得用真阳引回去,《金匮要略》说病痰饮者,当以温药和之,就是这个理。"
说话间,药方已经开好了。岐大夫指着纸上的字解释:"附子、干姜、肉桂是给你添柴火的,这三味药性子烈,就像寒冬里的炭火,能把沉下去的阳气拽上来。党参、茯苓、白术是帮着你家灶王爷干活的,脾胃气足了,才能把水谷变成津液。"他又点了点龙骨、牡蛎、乌梅,"这几味是收东西的,把补起来的阳气好好收在身子里,别让它散了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