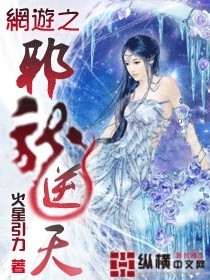泥巴文学 > 末日尘埃 > 第388章 断片的记忆(第1页)
第388章 断片的记忆(第1页)
夜像被墨汁反复涂过,黑得没有一丝缝隙。
不知过了多久薛羽睁开眼,天花板的白炽灯被调到最暗,仍刺得他瞳孔骤缩。空气里浮着消毒水与冷气机金属混合的味道,像一条无声流淌的河,把他从混沌的深渊慢慢推回岸边。
他侧过头。
窗外是一方狭长的景——黑黢黢的树影在远处围墙外摇晃,路灯的光晕被雨丝切割成碎银;更远处,停机坪的导航灯排成幽蓝的串珠,一闪一闪,像在提醒他:这里是军区附属医院的C栋,五楼,特护503。
既熟悉,又陌生。
熟悉的是——那排灯、那道围墙、那棵歪脖子樟树,他曾无数次在归队时掠过;陌生的是——此刻的自己,像被硬塞进一幅旧画里的新色块,边缘毛糙,格格不入。
“我是谁?”
念头刚冒出来,舌尖便尝到苦涩的铁锈味。
“我在哪?”
喉结滚动,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。
轰——
夜空骤然裂开,一连串闷雷滚过屋顶。
闪电的白刃把病房照得雪亮,也照出他额角细密的冷汗。
紧接着,三颗小黑点划破远天,拖着幽蓝的离子尾焰,俯冲、减速、稳稳降落在停机坪。那是凌晨紧急返航的无人运输机,机腹下的红色指示灯像三颗凝固的血珠。
雷声滚过,茫然像被利爪撕开的薄纱,瞬间褪得干干净净。
薛羽猛地坐起,心电监护仪发出短促的“嘀嘀”警报。
咔哒。
值班护士推门的动静轻得像猫,却在寂静里炸出涟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