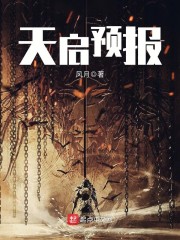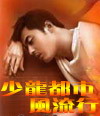泥巴文学 > 岐大夫的悬壶故事 > 第338章 螃蟹惹的祸与透郁的黄连(第1页)
第338章 螃蟹惹的祸与透郁的黄连(第1页)
秋分刚过,岐仁堂后院的菊花开得正盛,紫的、黄的、白的,攒在青砖墙角,把药香都染得带了点清苦的甜。岐大夫坐在前堂的竹椅上,手里摩挲着本清刻本《伤寒论》,阳光透过雕花木窗,在泛黄的纸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"师父,这黄连得用酒炒吗?"徒弟小杨蹲在药碾子旁,正碾着一堆黄澄澄的黄连,细小的粉末沾在他鼻尖上,像落了点金粉。岐大夫抬头笑了:"炒黄连得用米酒,小火慢炒,炒到外皮带点焦斑就行。《本草纲目》说黄连得酒引之上行,本来它专清胃火,炒过了能顺着肝气走,专治那郁在里头的火气。"
话音刚落,门口的铜铃"哐当"响了一声,撞得比平时都急。一个穿蓝布褂子的中年男人扶着个面色发青的人进来,刚到门槛就踉跄了一下,差点绊倒——扶人的是街口"文渊书店"的老板娘刘桂芬,被扶的是她丈夫,书店老板包文轩。
包文轩这模样,岐大夫看着心里一紧。这人平时总穿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戴副黑框眼镜,说话慢条斯理的,最爱在书店门口摆个小马扎,跟老街坊聊《红楼梦》。可今天他嘴唇发紫,额头上全是冷汗,双手死死按着肚子,腰弯得像只对虾,每走一步都"嘶"地吸口凉气。
"岐大夫,您快救救老包!"刘桂芬把丈夫扶到诊床上,自己急得直搓手,蓝布褂子的袖口都磨得起毛了,"这都疼了一个多月了,越来越厉害,刚才在家疼得直打滚,手脚冰凉,跟摸冰坨子似的!"
包文轩勉强抬起头,眼镜滑到鼻尖上,他也顾不上推:"岐大夫。。。。。。疼。。。。。。就像有把锥子在肠子里头拧。。。。。。"话没说完,疼得浑身一颤,额角撞在床沿上,发出"咚"的一声。
小杨赶紧递过个枕头垫在他腰后,岐大夫已经搭上了脉。三指按在寸关尺上,凝神片刻,眉头慢慢皱起来:"脉沉在底下,数得像打小鼓,这是沉数脉啊。"他又翻了翻包文轩的眼皮,眼白上布满红血丝,再看舌苔,舌质红得发紫,苔黄腻得像抹了层芝麻酱。
"桂芬,他这病是怎么起的?"岐大夫松开手,从药箱里拿出个小陶罐,倒了点温水给包文轩漱口。刘桂芬叹口气,搬了个板凳坐在床边,一五一十地说起来——
这病得从一个月前说起。那天是包文轩五十岁生日,女儿从城里回来,拎了一篓阳澄湖大闸蟹,说是"给爸补补"。包文轩这辈子爱吃蟹,尤其秋天的蟹膏最厚,那天他就着姜丝喝了两盅黄酒,一口气吃了四只。
"我就劝他少吃点,"刘桂芬抹了把眼角,"他说一年就这时候的蟹最肥,结果半夜就出事了,肚子疼得直哼哼,跑了三趟茅房,拉的全是稀水。"
第二天一早,她陪包文轩去了社区医院,坐诊的王医生说"准是吃凉了",开了平胃散和二陈汤,说"这两剂药能燥湿化痰,把胃里的寒气逼出去"。药吃了三天,拉肚子是好了,可肚子疼没见轻,反而变成一阵一阵的绞痛,疼起来直冒冷汗,不疼的时候又跟没事人似的。
"后来王医生又说,准是寒气没除干净,"刘桂芬声音发颤,"给换了理中汤,还加了生姜、肉桂,说这药劲儿大,准能把寒气连根拔了。可吃了没两剂,老包这疼得更邪乎了,不光肚子疼,连两胁都胀得跟塞了棉花似的,夜里疼得没法睡,蜷在床上像个虾米。。。。。。"
"那手脚冰凉是咋回事?"小杨忍不住插话。刘桂芬往包文轩手上瞅了瞅,他的手现在还凉得吓人,指甲盖泛着青紫色:"疼得最厉害的时候就这样,脚底板凉得像踩在冰窖里,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热。王医生说这是阳虚,又加了附子,结果越吃越重。。。。。。"
包文轩这时缓过点劲,喘着气说:"昨天。。。。。。昨天试着喝了口热粥,刚下肚就疼得差点背过气。。。。。。"
岐大夫听完,拿起桌上的茶壶给刘桂芬倒了杯茶:"您先别急,我给包先生查查。"他让包文轩平躺,手指轻轻按在他腹部:"这儿疼得厉害?"按到肚脐周围时,包文轩"嗷"地叫了一声,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。再按两胁,他疼得直摇头,说"像有气在里头窜,胀得慌"。
"小杨,记下来。"岐大夫直起身,"腹痛阵作,痛时手足厥冷,两胁胀痛,拒按,纳差,舌红苔黄腻,脉沉数。"他转向刘桂芬,"包先生这病,根源确实在吃螃蟹上,但不是寒气没除,是寒气郁在里头,变成火了。"
"火?"刘桂芬眼睛瞪得溜圆,"他手脚凉得像冰,咋会是火呢?王医生一直说他是寒。。。。。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