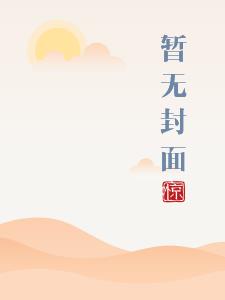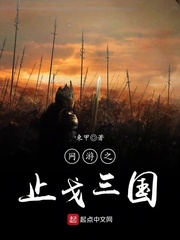泥巴文学 > 岐大夫的悬壶故事 > 第338章 螃蟹惹的祸与透郁的黄连(第3页)
第338章 螃蟹惹的祸与透郁的黄连(第3页)
小杨手脚麻利,没一会儿就把药抓好了,用草纸包成方方正正的一包,上面用毛笔写着"每剂水煎两次,温服"。刘桂芬接过药包,沉甸甸的,纸包里透出一股清苦的药香,混着点米酒的甜气。
"师父,包先生这情况,真能一剂就好?"等刘桂芬扶着包文轩走了,小杨忍不住问。岐大夫正用布擦着脉枕,慢悠悠地说:"《伤寒论》里说病皆与方相应者,乃服之。只要辨证准了,药证相符,效如桴鼓也不稀奇。但也别大意,明儿一早你去看看,要是疼减轻了,就把黄连减点量,加两钱茯苓,免得苦寒伤了脾胃。"
第二天一早,小杨刚把药柜的抽屉拉开一半,就听见门口传来刘桂芬的大嗓门:"岐大夫!神了!真是神了!"她手里提着个竹篮,脚步轻快得不像昨天那个愁眉苦脸的人。
"包先生咋样了?"岐大夫放下手里的《金匮要略》。刘桂芬笑得眼角堆起褶子:"昨天中午喝了头煎药,下午就说肚子里咕噜响,放了几个屁,那胀疼就轻多了!晚上喝了二煎,夜里居然睡了个安稳觉,今天早上起来,说饿了,喝了小半碗稀粥,一点没疼!"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她掀开竹篮,里面是个白瓷碗,盛着刚蒸的米糕:"这是老包让我送来的,说谢谢您的救命药。他现在能自己走动了,手脚也暖和过来了,就是还有点没力气。。。。。。"
正说着,包文轩跟在后面进来了,虽然脸色还有点苍白,但眼睛亮了,腰也挺直了些,走路不再捂着肚子。"岐大夫,真是谢谢您。。。。。。"他声音还有点虚,但语气里满是感激,"昨天喝药后,就觉得一股气从两胁往上升,打了几个嗝,那疼就跟退潮似的,一点一点下去了。"
岐大夫给他搭脉,这次的脉虽然还偏弱,但沉数之象已经缓和了许多,舌苔也没那么黄腻了。"这就对了,"他点点头,"郁气散了,火气清了,脾胃就能慢慢恢复。今天再服一剂,黄连减成一钱,加茯苓三钱,健脾渗湿,免得郁火伤了津液。"
小杨在旁边写方子,忍不住问:"师父,那为啥王医生用的药会不管用呢?"
岐大夫指着窗外的菊花:"你看这菊花,要是浇太多热水,准会蔫了;可要是光浇凉水,又长不好。看病跟养花一样,得辨明虚实寒热。包先生这病,表面看是寒,骨子里是郁火,就像冻在冰里的火种,得先化冰,再引火,不是一味添柴就行。"他拿起《伤寒论》,"张仲景为啥把辨病脉证并治放在最前头?就是说看病得先辨清楚病性、病位,不然药不对证,不是杯水车薪,就是火上浇油。"
包文轩坐在一旁,听着这话,若有所思地说:"其实。。。。。。我这病也怪自己。那天吃螃蟹时,就跟女儿拌了两句嘴,心里憋着气,结果吃下去的蟹肉就跟堵在心里似的,现在想起来,那时候就有点隐隐作痛了。。。。。。"
"这就对了。"岐大夫赞同道,"《黄帝内经》说怒则气上,喜则气缓,悲则气消,恐则气下,惊则气乱,思则气结。七情太过,最容易伤气。你爱琢磨事,思则气结,再加上动了怒,肝气郁结,这不就给寒气可乘之机了?以后遇事别钻牛角尖,气顺了,病就少了。"
包文轩连连点头,眼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推:"您说得是,以后我得多出来走走,少跟自己较劲。对了,岐大夫,您这医理讲得透彻,我想把这次的经历写下来,贴在书店门口,让老街坊们都学学这养生的道理,行不?"
岐大夫笑了:"这是好事。中医治病,不光是给药,更是给个明白。让人知道病是咋来的,该咋防,比啥都强。"
那天下午,阳光正好,岐仁堂的药香混着隔壁面馆飘来的葱花味,在老街上慢慢散开。小杨蹲在药碾子旁,继续碾那堆黄连,嘴里哼着新学的《汤头歌》:"四逆散里用柴胡,芍药枳实甘草须。。。。。。"岐大夫坐在竹椅上,翻着《脾胃论》,嘴角带着笑意——这医案,又能给徒弟讲阵子了。而街口的文渊书店门口,后来真的贴了篇包文轩写的《吃蟹记》,字里行间都是对中医的叹服,也提醒着老街坊们:这吃东西啊,不光要看性味,还得看心气,心气顺了,吃嘛嘛香。
喜欢岐大夫的悬壶故事请大家收藏:()岐大夫的悬壶故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