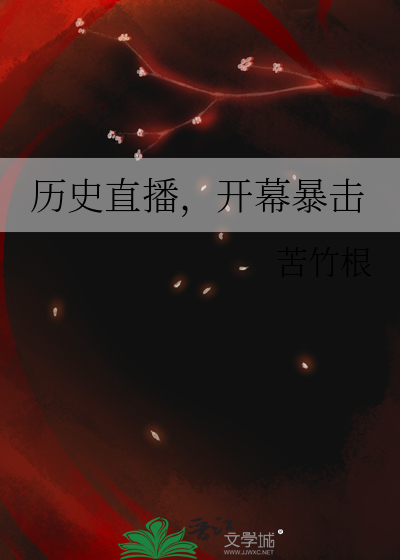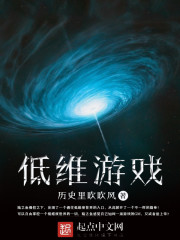泥巴文学 > 岐大夫的悬壶故事 > 第334章 秋痢惊魂:岐仁堂的附子香(第1页)
第334章 秋痢惊魂:岐仁堂的附子香(第1页)
一、菜市场里的“拉肚子”
九月的风已经带了凉意,老城区的早市却热闹得冒热气。江德才蹲在自家的豆腐摊后,看着来往的人潮,心里盘算着今天能卖多少块嫩豆腐。他今年六十二,退休前是机床厂的师傅,手巧,退休后闲不住,跟着老伴刘桂英支起了这个豆腐摊,黄豆是乡下亲戚送的,磨得细,点得匀,在这条街上小有名气。
“老江,来两块嫩豆腐!”隔壁卖葱姜的王大爷吆喝着,手里还拎着刚买的秋梨,“今年秋燥,我家那口子说要炖点梨汤。”
江德才笑着应着,用竹刀麻利地切下两块白玉似的豆腐,裹上油纸:“秋分都过了,是该吃点滋润的。我昨儿也买了俩柿子,甜得很。”
收摊回家,刘桂英已经焖好了米饭,炒了盘青菜,还端上一碟酱瓜。江德才洗了手,拿起昨天买的柿子,刚咬了一口,就被刘桂英拦住了:“刚从早市回来,一身凉气,先喝点热粥暖暖。”
“没事,这柿子软乎。”江德才满不在乎,几口就把柿子吃了,又扒拉了两碗米饭,喝了半碗菜汤。
当天夜里,江德才就不对劲了。后半夜,他突然觉得肚子疼,像有无数只小虫子在肠子里钻,一阵紧似一阵。他捂着肚子冲进厕所,刚蹲下就泻了起来,稀里哗啦的,全是水,还带着点黏糊糊的东西。
“咋了?”刘桂英被吵醒,披着衣服过来问。
“闹肚子……”江德才的声音有气无力,额头上渗着冷汗。
这一晚上,江德才几乎没离开厕所,一趟趟地跑,到后来,腿都软得站不住,拉出来的也不再是水,而是夹杂着红色黏液的东西,腥腥的,闻着让人反胃。
第二天一早,江德才脸色蜡黄,眼窝都陷了下去,浑身没劲,往床上一躺就起不来了。刘桂英赶紧去社区医院请了张医生来。
张医生给江德才量了体温,38度多,有点发热。又问了症状,听说是又拉又吐(后半夜开始有点恶心反胃),还带着脓血,皱着眉说:“这像是痢疾,秋天最容易得。”他开了些清利湿热的药,有黄连、黄芩、白头翁之类的,嘱咐刘桂英:“多给他喝点淡盐水,别脱水了。要是还止不住,就得去大医院输液。”
药熬出来是苦绿色的,江德才喝一口就想吐,强忍着才灌下去。可药喝了两天,病不但没好,反而更重了。
拉肚子的次数越来越多,一天能有几十次,甚至上百次,有时候刚躺到床上,肚子一疼就得往厕所跑,根本来不及。拉出来的全是赤红色的黏液和脓血,腥秽难闻,像是烂肉汤。他一点东西也吃不下,喝口水都吐,嗓子眼干得冒烟,一个劲喊渴。身上的热也没退,脸烧得通红,嘴唇却干得起了皮。
刘桂英看着老伴一天比一天消瘦,眼瞅着就脱了形,急得直掉眼泪。社区医院的张医生又来了两次,药也调了几次,加了些止泻的,可都不管用。“不行啊,”张医生看着江德才虚弱的样子,也有些犯愁,“这痢疾太顽固,要不还是去大医院吧,输点液补补水分。”
江德才迷迷糊糊的,听见去医院,摆了摆手:“不去……去岐仁堂……找岐大夫……”他年轻时得过一次胃病,就是岐大夫的父亲给看好的,心里总觉得老中医靠得住。
刘桂英也听说过岐仁堂的岐大夫,七十多了,看疑难杂症很有一套。她咬了咬牙,决定听老伴的,赶紧让儿子去请岐大夫。
二、冷汗淋漓的危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