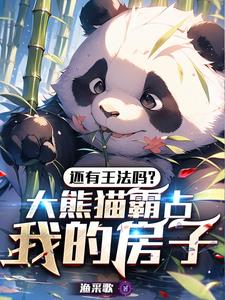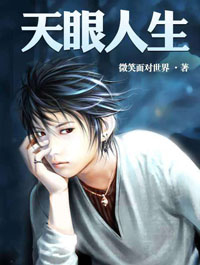泥巴文学 > 岐大夫的悬壶故事 > 第337章 堵心的工程款与救命的附子(第3页)
第337章 堵心的工程款与救命的附子(第3页)
当晚,岐大夫没回家,就在药铺的隔间守着。夜里陈玉山又醒了一次,说右胁疼得轻了些,还想吃口米汤。小杨在旁边记医案,写道:"服附子理中汤半剂,得进米汤两口,未再呕吐,脉息稍复,阳气初回。"
第二天一早,陈玉山居然能自己坐起来了,虽然还没力气说话,但眼神亮了些。岐大夫又给他诊脉,这次重按之下,隐约能摸到点搏动了,不像昨天那样空落落的。"有起色了。"他对周敏说,"今天的药减点附子量,加片生姜,生姜能和胃止呕,就像给胃气搭个梯子,让它顺顺当当往下走。"
这天陈玉山喝了小半碗米汤,中午时解了次大便,虽然还有血,但颜色淡了些,不再是黑红色。周敏高兴得直抹眼泪,跟送饭来的工友说:"岐大夫真是神了,医院都没办法的事,他两副药就见好!"
工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。瓦工老王说:"我去年也气得胃疼,吃了些顺气的药不管用,后来岐大夫让我用陈皮泡水喝,说气顺了就不疼了,还真管用。"钢筋工小李插嘴:"我爸也脾虚,岐大夫让他多吃炒山药,说山药能补脾气,就像给土地上肥,现在身体硬朗多了。"
岐大夫听见了,笑着说:"不是我神,是中医讲顺其性。人就像庄稼,该浇水时浇水,该施肥时施肥,别逆天而行。陈经理这病,就是违背了脾喜温恶凉,喜燥恶湿的性子,又让肝气伤了它,现在不过是帮它回到正道上。"
接下来的五天,陈玉山的药每天都微调:第三天加了茯苓,说"脾土虚了容易生湿,得加点渗湿的";第五天减了干姜,加了点炒麦芽,"胃气醒得差不多了,该让它自己动起来,麦芽能消食健胃,就像给脾胃加个小马达"。到第七天时,他已经能喝小半碗小米粥,还能跟周敏说两句话,讨论工地的事了。
"师父,现在能换方子了吗?"小杨看着陈玉山气色好转,问道。岐大夫正在翻《金匮要略》,指着其中一页说:"《金匮》讲病痰饮者,当以温药和之。他现在阳气回来些了,但脾土还虚,得慢慢补。附子理中汤是救急的,就像给冻僵的人猛灌姜汤,现在缓过来了,该换温和的方子,六君子汤就合适,还得配上金匮肾气丸,脾肾同补。"
这次的六君子汤,岐大夫加了炒白芍和柴胡。"白芍能柔肝,就像给太旺的肝气撒点水;柴胡能疏肝,好比给打结的绳子松松劲。"他解释道,"肝脾得互相照应,肝不欺负脾,脾才能好好干活,这叫土得木而达。"
周敏每天来取药,都会带来陈玉山的消息:"今天能吃一个馒头了能下地走两步了昨晚跟我念叨,说等好了,一定请您去工地食堂吃炖排骨"。岐大夫总是笑着说:"让他先养好脾胃,排骨得烂烂的才好消化。"
一个月后,陈玉山能自己走到岐仁堂了。他穿着件干净的衬衫,虽然还瘦,但眼神亮了,走路也稳当。"岐大夫,您这药真是救命的。"他坐下时,不再用手撑着胸口了,"工程款的事也解决了,甲方查清楚是监理从中作梗,钱给了,还赔了道歉。"
岐大夫给他搭脉,这次的脉虽然还偏弱,但已经沉稳有力,不再是空弦之象。"您看,这脉就像雨后的土地,虽然还软,但有了生气。"他欣慰地说,"《黄帝内经》说恬惔虚无,真气从之,以后少生气,按时吃饭,比啥药都管用。"
陈玉山点点头,从包里掏出个红布包,打开是面锦旗,写着"妙手回春,仁心济世"。"这是工友们凑钱做的,说您不光救了我,也让大家明白,身体比啥都重要。"
岐大夫把锦旗挂在堂屋正中,正好在"岐仁堂"匾额的下方。那天傍晚,夕阳透过老槐树的叶子照进来,锦旗上的金字闪闪发亮,药柜里的当归、黄芪散发出淡淡的药香,和着窗外飘来的饭菜香,让人心里踏实。
小杨在整理医案,问:"师父,这陈经理的病,关键就在那个附子吧?"岐大夫拿起块炮制好的附子,掂了掂:"附子是救命的,但救回来还得靠养。就像种地,不光要施猛肥,还得勤浇水、多除草。中医治病,从来不是只靠药,是靠顺应天地规律,顺应身体本性啊。"
他望着窗外,老槐树下,几个孩子在追跑打闹,笑声清脆。远处传来工地的塔吊声,嗡嗡的,很有节奏。岐大夫拿起《脾胃论》,在"人以脾胃为本"那页轻轻折了个角——这故事,够小杨学一阵子了。而陈玉山的故事,也会像这药香一样,在老街坊的嘴里,慢慢传开去。
喜欢岐大夫的悬壶故事请大家收藏:()岐大夫的悬壶故事